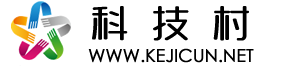本文基于2024年6月30日能效电气创始人汪进进对话环球网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专访对话录音,参考“百城百讲”充电桩科普讲堂的演讲及此前发表的公开文章,由汪杨整理,以能效电气创始人汪进进第一人称方式叙述,初创团队成员进行事实性审阅。
题记
“窄门和窄路引向永生,只有极少数人才找得到”。
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6年,电动汽车及充电桩产业在沉寂多年后倏然兴起。国家相继出台了各类电动汽车和充电桩的补贴政策。一时之间,“猪飞的声音”响彻中华大地。
2016年,能效电气从研发双向充电模块的“窄门”做起,持续创新,在火热的新能源行业长河穿过。这里是能效电气留下的第一视角。
过去
1. 华为爱默生的记忆
2001年中国加入WTO,深圳开始步入了一辆高速行驶的快车。2002年,我硕士一毕业就来到了深圳,入职艾默生。那一年,艾默生刚收购华为的电源业务,完成了震惊业内的电力电子产业大并购。
2002年4月19日下午1:48,我千里迢迢孤身一人来到深圳西火车站,在尘土飞扬中坐上了204大巴到科技园站台,然后辗转半个多小时找到K2(现在车次应该改名叫339了)公交车站, 过了1个多小时到达百草园,那是当时很多年轻人梦想的地方。我是那批入职的40多位毕业生中唯一坐绿皮火车到来的。毕业前我没有坐过飞机也没一个人坐过火车。为了赚一点差价,我选择了绿皮火车(不管坐什么交通工具, 公司都报销1500元, 但公司鼓励坐飞机,只在机场有接站)。
在来深圳的火车上,我认识了一位热心人,他带领我到204公交站台并很客气地抢着帮我付了公交车费。
他看出我对尘土飞扬的西火车站感到有点失望,于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打工妹来到深圳,在火车里看到窗外是这么破烂,坚持不下车,说这不是她心中的深圳…… 当年,深圳西站门口非常破烂。现在,深圳西站已经拆除了。
那时候加入的公司还叫安圣电气(安圣电气之前叫华为电气),还没有完成并购后的切割,还住在百草园, 还戴着华为工卡,用华为电子流。那时候华为人以戴着工卡去百草园的华润超市潇洒购物而自得,甚至还有的坐公交车都戴着工卡的。老任当年为了获得过冬的棉袄(也有说法是为了一次性处理掉一批烂帐,走出野蛮生长阶段),获得了现金流,也为中国电源行业输入了一批创业者。
有一天,有位老员工指着那个48V/50A的电源模块骄傲地告诉我:“你知道这个东西,我们以前称它什么吗?”, “ 称为“金砖”,一个能卖2万元,爽死了!”。“电源是金砖”的年代仿佛是久远的过去。
但其实,中国真正做出了48V/50A通信电源并实现了商业化只是在20世纪90年中期(具体是哪一年我没有考证了)。那时华为能做出48V/50A,打破了“八国联军“的封锁(爱立信等外资企业的电源产品),3kW电源的价格一下子被降到2万元以内。
那时候的艾默生基本上还是华为文化,但老员工却在那时候开始概叹,如果是在当时的华为,现在该怎么样怎么样了。在112年的百年老店艾默生工作,公司强调“家庭第一,工作第二”,外人看起来很幸福的老员工却常常怀念在任老板统治下的艰苦岁月。
当年刚进华为的时候,我在测试部先实习三个月,我的师傅方宏苗比较冷幽默,有天他突然问我,“你见过教员吗?”, 我一下子怔住了,他笑着说,“我见过!任老板就是教员。”
任以极其低调著称,但在华为内部是绝对的思想领袖。他不搞个人崇拜,但在那时华为人心中他就是“教员”。
当华为人谈到,“假设老任不在了,世界将会怎样?” 空气突然凝滞。也只有很要好关系的朋友会私下谈谈。按我们家人迷信的说法,对于不吉利的事情,提都不要提,如果提了,老人要小孩自己打一下自己的嘴。
若干年后,我的那些老同事肯定还会对他大学毕业的儿子说, 当年老子进华为的时候,通信电源还是“八国联军”(90年代初,开关电源技术还没有在中国产品化,特别是高端的通信电源,只有八家著名的外资企业可以做出来),
我参加了公司第一个数字电源(整流器)预研项目,敲了数字电源的第一行代码,预研成功后转到了项目组。那自豪感可以作为“夕阳红”时的父子传承。
有时侯我就想,“崇尚奋斗”这有什么错吗?人生啊,一生中有那么一段兴奋的充满激情的时光总是值得被铭记的。
辞职前,同事说这工卡有收藏价值,有同事就故意挂失工卡。我也就在辞职前挂失了一下,可惜那保留的工卡搬家几次给弄丢了,想想蛮可惜的。
我于2004年10月离开了艾默生, 但那段研发电源产品的时光对于我的帮助确是终身受益的。
后来我逢华为书(写关于华为的书)必买,这个习惯保持到2012年。我实在坚持不了了,因为看不下去了,太相似了,觉得不如自己写了,而且有的写得也扯淡得很。专业写手的文笔不是我可以比的,但他们缺少对华为的真正的理解。
不怕大家笑话,2016年元旦这天我到深圳的龙岩古寺游玩,看到有众人在求签,我也就求了一支。猜猜我在求签时内心问菩萨一句什么话了吗?说出来羞煞自己。
我问菩萨,“我可以成为中国某某界的任正非吗”?
菩萨给了我一个个下下签。我语文学得不好,看到签的第一眼,以为是上上签,花了10元找了个解签的道士,他告诉我是下下签——我自以为是,把菩萨的意思理解错了。
道士要我花99元买一道“仙符”,和这下下签一起烧了,再上几柱香拜一拜,以求菩萨保佑,菩萨可以将下下签化解为上上签。我从小是反对迷信的,但这天我真的花了99元烧了一道求苍天保佑之“仙符”。
那天我泪湿沾巾。记录下这个片段作为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记忆之一。那个寺庙将成为我记忆的一个地标。也许,30年后我可以去“还愿”吧,还一个小人物的大愿望。
2.充电桩行业没有机密
从无比热闹,到一地鸡毛,再到无比寂寞
在2002年,老员工常叹道:做电源没啥意思了,是夕阳行业了,不赚钱了,有些电源1瓦只能卖1元了。但是,这帮不看好电源利润的家伙后来一个个都去创业,做电力电子行业的老板去了。现在一提起艾默生系:“某某是艾默生出来的!” 提起华为、爱默生,感觉很荣光。
后面很多从华为艾默生系走出来的人都纷纷创业或跳槽,催生了深圳电力电子产业链。华为艾默生是电源届的黄埔军校,是成就A股最多上市公司的创业群体,有十多家公司在A股上市。
论及中国电力电子行业,如果没有2001年底华为将电源部门卖给艾默生这个章节,现在的故事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当然,不是说这帮人继续在华为就一定不去创业,但创业的成本会高很多很多,创业的成功概率也就小很多。因为,从华为出来创业,直接和华为竞争,容易被老任给捏死。
但对于刚把华为卖给像是艾默生这样的大型外资企业,所有人都是“打工的”,正在打工的公司的奶酪被动了之后,还会想:“哇,原来可以这样快速获得美味的奶酪,我也可以试试”。
从华为艾默生出来后,我陆续接受了美企德企大企业长达十几年的职业训练,后面又去了一家做示波器的民企。2016年,我选择了”半创业“,似乎有一个执念一直在驱使着我。我觉得应该抛下过往,重新开始。该创业了。
同年,中国有很多相关创业者、半创业者。我的一位师弟也和我一样,2016年开始做充电桩,他在一家上市公司干,很快,在2017年,他就实现了两个亿的营收。他当年销售费用就占了营收的45%。
能效电气(包括前身)从2016年到2021年,销售费用只有0.5%,但研发费用却是30%以上,一直只有1个商务兼平面设计,2个销售(包括我自己),1个项目经理(我本人),1个采购及研发助理,8个仓库(厕所门口左边1个,右边1个,车间里4个,露天1个,真正的仓库1个。现在回忆,这种寒酸真的不忍心)。
有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只招收了研发和销售相关的人员,但是就不敢多招聘一个商务,多招聘半个采购,更奢谈招专职项目经理、大客户销售。我们按照30年前创业的土方法,将1分钱当作1万元钱花的方式,在死人堆里一直爬行了八年,一直埋头专注于研发核心技术,自研充电模块,自研充电控制器,自研后台。
6年坚持爬行模式,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家企业应该有自己的技术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是一砖一瓦慢慢建立起的。
充电桩行业的无比热闹期是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那三年,可以靠什么赚钱呢?就是用一个相同外观的整桩,换不同铭牌去拿型式试验报告。他的客户拿到报告后参加地方招标。
飞起时的景象就是这样。
放眼充电桩市场,最热的时期一般是16、17、18年,那时补贴特别高,而且政府还能兑现补贴。很多人为了补贴去建充电站,后来有人拆了桩又去骗新的补贴。那时候建起来的充电站,后来都赚到了钱。
但是现在进入市场却是很辛苦了,不管是中字头的中国石化、中石油来收购这些充电站的运营商,还是把充电桩当做摇钱树的运营商,还是进来做硬件设备,卖充电桩的厂商,由于竞争白热化,现在都很辛苦。
很多年以前,深圳山寨白牌手机兴起,有一个女老板杀出了重围,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她成功地坚持了下来。然后,随着苹果在2007年发布智能手机,山寨智能手机和山寨笔记本电脑的,全都失败了。稍微复杂一点的产品,我理解,单单靠“山寨”贴牌做生意是无法长久的。
终局思维
“终局思维”,简而言之,就是学会“倒着思考”,预期3年、5年甚至10年的未来,再来确定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我经常讲,我把充电桩企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进来打酱油的上市公司
比如正泰、海尔的卡泰驰,还有其他一些做电相关行业的企业,他们听说这个行业不错,就想进来试试,结果浅尝辄止,做了一段时间可能就放弃了,很快撤掉了,因为竞争太激烈。也有的坚持下来了。
其实这些公司里能用的人才并不多。在中国,能够开疆拓土的职业经理人很难找到。大公司如果遇到一个能干的将才,市场还不错,就会觉得这个市场挺好,一股脑的就进来了,过了几年,发现没赚到钱,又放弃了。
第二种是投机取巧的企业
主要是面向政策或招标型市场,满足物业配套或者政府行政项目的需求。这些企业的问题很大,风一吹就会倒下。政策变化或者招标结束后就会出现问题。听说在郑州有七家做交流充电桩的企业,去年有三家发不出工资了。
第三种是质量型的市场选手
我把我们归为这一类。质量型企业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的长远发展。比如蔚来的一个小直流充电桩有8100多个物料,而交流充电桩一般只有200多个物料。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的区别就像豪华汽车和儿童手推车的区别。
看似简单的东西,实际上隐藏了很多技术含量。质量口碑的背后是大量的努力和投入。
从终局思维来看,我认为那些打酱油的和投机取巧的企业终将会离开这个市场。理解这种终局思维很重要。譬如我们现在称120kW的市场为一个长期的市场,许多第一批进入市场的中小运营商开始更新换代,一般来说,五年的设备就需要淘汰了。这意味着,这些企业会逐渐选择更高质量的产品,而我们的产品正是他们需要的。
这几年来,那些靠“投机取巧”,以作坊店成本搞低价的小玩家,在竞争白热化的市场里,很快销声匿迹了。
靠纯商务能力做招标型市场的玩家也因难看的资产负债表进退两难。“打酱油”的上市公司,仰望资本力量和品牌横溢的玩家,销声匿迹了一批,又进来新的一批。
“投机取巧”是人性。投机取巧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最终还是要依靠踏实的努力和长远的规划才能在这个行业立足。一直以来,在行业长河中,留下来的,最后还是那些专心“磨豆腐”的。
充电桩行业作为新能源赛道的衍生行业,很新也很小,是风口上的“猪”。有大的资本和小的公司频频进入进出。在这个热闹又孤独的舞台上,需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匠人精神。
2016年、2017年、2018年充电桩行业火热了一阵子,然后迅速冷却下来。放眼过去几十年,中国每个行业都是从无比热闹,到一地鸡毛,再到无比寂寞。光伏也是这样,LED也是这样。
这是制造业通律,是常识。
“这种通病是中国制造业的痛苦,还是全球制造业都有这个问题?”
有记者听到我这话,睁大眼睛问我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是谈民族性格,还是谈人性。
我觉得这是人性问题,投机取巧的人永远有很多,愿意长期踏踏实实干活的永远是少数。这是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我在大学二年级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从那后开始,我有了一个信念:“改变一个人胜于改变整个世界”。我不能试图靠单纯的热情去改变一个人一些内核的东西,譬如价值观。因此,我只寄希望于能找到和我持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人们,一起快乐和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我的创业初衷。
编辑:yezi